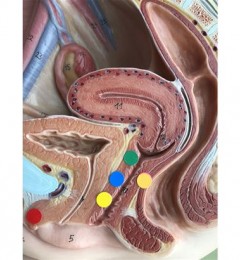我18岁时吞下人生第一颗抗忧郁剂。那天,阳光微弱,我站在伦敦某购物中心药局外头。药锭是白色的,小小一颗,吞下后会感受到一个化学的亲吻。
那天早上,我去看医生。我跟他说,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有哪一天不想哭。打从小时候——在学校、大学、在家或跟朋友在一起时——我常必须抽离一下,把自己关起来哭。那种哭,不是滴个几滴泪而已,而是踏踏实实地哭。即使没掉泪,我心中仍不断响起焦虑的独白。我会自责:都在你脑里。要跨过去。不要这么懦弱。

这一切,让我当时不好意思谈起,现在也羞于敲键托出。
如果有人问,我会跟他们解释忧郁症是大脑疾病,解药是“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(SSRIs,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)”。后来当了记者,我在报上撰文对大众耐心说明。我将持续回流的悲伤解释成治疗过程的必经之路——大脑里的化学物质会用尽,无法控制也无从了解。我会说谢天谢地,药物很有效。看看我,我就是实例。虽然脑袋里经常会质疑,但只要多吞一两颗药,疑问就快速抛在脑后。
我自有一套说帖。其实我现在知道,这个说帖分两部分。首先是忧郁症病因——大脑失能,血清素浓度不足或大脑硬件出了乱子。第二是解药,也就是药物,药物会修复脑内化学状态。
我喜欢这个说帖。这说帖对我来说是合理的,也引领着我的生活。
三年前我开始写这本书,因为我还是有些谜题没有解开。那些谜,是我长期信服的那一套所无法解释的,我想找出答案。
来谈第一个谜。服药了几年后,某天我坐在诊间,向治疗师诉说我感激抗忧郁药物的存在,让我快活。他说,“怪了,我看你还是忧郁呀。”我不懂他的意思。他继续说,“你常常都是忧郁的。在我看来,跟你服药前的描述没有差太多。”
我耐心跟他说明那是他有所不知——忧郁症是血清素不足所引起,所以我要提高血清素浓度。我心想:“这些治疗师到底受过什么训练了?”
这些年,他不时会温和地提出这一点。他说,提高剂量就会迎刃而解的想法与事实不符,因为我多数时间还是心情低落,充满着忧郁和焦虑。
过了好几年,我终于听懂他当时说的话。因为,吃再怎么高的剂量,抗忧郁药物都压不住我的悲伤。一开始,化学制剂确实有明显的缓和效果,但当那个防护泡泡散去,刺痛的不愉悦感会再度回来。强烈的念头不断出现,说着人生了无目的,所做的一切不具意义,只是浪费时间。焦虑感挥之不去。
因此,我想了解的第一个谜是:为何服用抗忧郁药物还是会忧郁?我样样做对了,却还是有些不对劲,原因何在?
过去几十年来,有件怪事发生在我家。
打从小时候,我就有印象厨房桌上有好几个药罐,上面有我看不懂的白色标签。我写过家中有药物成瘾的问题,以及在我非常久远的记忆里我曾努力要摇醒亲戚,但没有成功。幼年时,主宰我们的生活并不是禁药,而是医生开的药——旧款抗忧郁剂和镇定剂,如烦宁锭(Valium)。有了化学物质帮我们微调,日子才过得下去。
我说的怪事是,随着我的成长过程,西方文明在用药这件事情上,追上了我们家。小时候跟朋友在一起时,我发现别人家并不会照三餐吃药。没有人用药物来镇定、鼓舞或对抗忧郁。我才知道,原来我家的状况并不寻常。
慢慢地,随着时间推移,药物在日常生活中愈来愈稀松平常,不管是医生开的、经核可的或建议服用的药物。时至今日,药物处处可见。在美国,每五位成人就有一人因心理问题服用至少一种药物,法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服用合法精神异常药物(如抗忧郁药),而英国可说是全欧洲用量最凶的。抗忧郁药物几乎让你无所遁逃——科学家在西方国家的自来水中发现抗忧郁药剂成分,因为抗忧郁药物的服用者众,排放后又无法从日常饮用水中过滤。确实,到处都充斥着这些药物。
昔日异事今已司空见惯。人们也没有多讨论,就接受了周遭很多人得用强效药物对抗忧郁,以正常过日。
我第二个疑惑是:怎么会多出这么多明显感觉忧郁和严重焦虑的人呢?是有什么改变吗?
31岁是我成年后第一次完全不吃药。治疗师的温柔提醒——我虽然持续服药,却仍觉得忧郁——我听而不闻了10年。一直到人生遇到危机,无法甩开坏心情,我决定要听他的。我把手上最后一包克忧果冲进马桶,觉得我心头的疑问像月台上等待接送的小孩,等待着我去注意。我为何依然忧郁呢?为什么这么多人跟我一样?
然后,我又发现第三个谜团:除了脑内化学物质失调外,有无其他原因会导致忧郁焦虑呢?
曾有好几年的时间,每当我开始研究这些谜题,看科学报告、和这些报告的作者对话,我就会退缩。因为他们说的事让我乱了阵脚,使我更焦虑。我在我的著作《追逐尖叫:横跨9国、1000个日子的追踪,找到成瘾的根源,以及失控也能重来的人生(Chasing the Scream: The First and Last Days of the War on Drugs)》有讨论这部分。听起来可能有点扯,我觉得访问墨西哥毒枭杀手比调查忧郁和焦虑的起因容易,推翻我用来解释我的情绪、感受和这些感受从何而来的说帖,对我而言是一种危险。
终于,我决定停止视而不见。于是花了3年,旅行6000多公里,在世界各地做了200次以上的访问,对象是全球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、历经忧郁和焦虑幽谷的人、痊愈者。我去了许多本来想都没想过的地方,如印第安纳州的阿米希村(Amish village)、柏林一个勇敢抗争的公宅小区、巴西某个禁止广告的城市,以及位于巴尔的摩、运用创新方法带领人们回溯创伤的实验室。这些见闻让我重新修正我的见解——对于我自己、对于蔓延在我们文化中的悲伤。
当我研究这9个忧郁和焦虑的起因时,我又有其他发现。过去,只要写忧郁和焦虑的文章,我会开宗明义地说:我不是在谈不快乐。“不快乐”和“忧郁”天差地远。对忧郁者来说,最火大就是有人叫你振作、开心一点,或教你开心的方法,彷佛你只是最近生活不顺遂。
我一面研究这些证据,一面又看到一件不能忽略的事。
会加重忧郁和焦虑的因素也会让人不开心。不开心和忧郁间有某种连结存在,但两者还是非常不同,就像因车祸失去一根手指跟失去一条手臂、仆街和坠落悬崖,都是不同但有关联的事件。
我逐渐明白,忧郁和焦虑像矛最尖锐的边缘,刺入我们文化中绝大多数的人。因此,本书的诸多内容,就算非忧郁或严重焦虑者也会觉得认同。















![俄罗斯的“天上人间”美女如云[组图]](http://www.xdjk.net/uploads/allimg/1112/4-111219151447-lp.jpg)